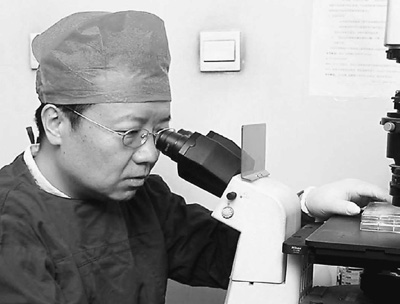
李文辉在观测实验结果。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供图
至今仍让全球2.4亿多人遭受痛苦的乙肝病毒,是美国已故科学家巴鲁克·布隆伯格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是目前全球顶尖的乙肝病毒研究机构。
前不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研究员李文辉应邀到该研究所做交流讲座。讲座后,巴鲁克·布隆伯格当年的助手,如今已白发苍苍的汤姆·伦敦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真的很高兴,你讲了40多年来我们一直想知道的事。”
只要这个课题有价值、有意义,就不该怕困难和风险
2007年10月底,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艾滋病和SARS冠状病毒研究的李文辉回国,到北生所另起炉灶,决定带领新招聘的助手和学生做令许多同行望而却步的课题——寻找乙肝病毒(英文简称HBV)受体。
乙肝病毒要想感染人类,必须先与细胞膜上的一个蛋白结合,然后才能进入宿主细胞,这个蛋白就是HBV受体。只有找到这个受体,才能深入了解乙肝的感染机制,进而研发出有效的治疗药物。
自乙肝病毒被发现以来,全世界许多顶尖科学家都在苦苦寻找它的受体。但是,40多年过去了,科学家们都无功而返。
“我可以做相对容易、好发论文的课题,但我想做乙肝病毒受体,因为它是这个研究领域最难也是最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李文辉告诉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即使最终我们可能做不出来。”
李文辉之所以做此决定,既源于他早年在国内医院实习时切身感受到的乙肝病人的痛苦,也因为这项工作巨大而迫切的现实需要:目前仍有超过2.4亿慢性乙肝患者,中国就约有1亿人携带乙肝病毒,其中慢性乙肝病人有3000万左右,每年约35万人死于慢性乙肝相关疾病。而当前已有的药物均不能根治乙肝,病人必须终身服药。
李文辉知道,做乙肝病毒受体难度极大、风险极高,很可能劳而无功。但是,他对王晓东说:“只要这个课题有价值、有意义,就不该怕困难和风险。”
“你都不怕失败,我们还怕什么?”王晓东说,“所里会全力支持你!”
整整4年团队还没有发表一篇论文,经历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课题选定之后,李文辉先带领学生们“打地基”。他们查找到国内外已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从里面辨别真伪、分析方法、总结教训,寻找可能提供启示的蛛丝马迹……
“地基”打得差不多之后,他们又购买来两只树鼩,试着把这种外形酷似松鼠的类灵长类小动物养活。原来,不同于其它病毒,乙肝病毒只能感染人类、黑猩猩和树鼩。根据分析,研究团队认为,在现有条件下,树鼩是唯一的突破口。于是,他们从树鼩的体内取出肝脏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建立研究乙肝病毒的体外感染模型,期望从中发现乙肝病毒的受体。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
乙肝病毒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病毒,直径只有40纳米。在几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负责乙肝感染的病毒蛋白看上去像一个大脑袋、短柄的毒蘑菇。它镶嵌在病毒包膜上,短柄儿前后4次跨过细胞膜。这一现象在病毒中非常特殊,很难用已有的实验体系进行研究。
在高通量测序中心帮助下,科研人员首先建立了树鼩肝细胞的基因表达图谱。之后,再通过各种手段分析,寻找树鼩肝细胞里可能与乙肝病毒结合的相关蛋白……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博士生严欢带队,用“鱼钩”把“小金鱼”(比喻乙肝病毒受体)“钓”上来;另一路由博士后钟国才带队,用排除法筛查。结果,几个月过去了,两路兵马均无功而返。
“是不是这个受体根本就不存在?”学生们陷入深深的困扰。
此时,时间已过去了整整4年,团队还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作为领队,李文辉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但经验告诉他:他们可能已经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在一次讨论会上,李文辉对学生们说:“这个受体是肯定存在的,只是它非常隐蔽,躲藏在很难察觉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去过,只是没有发现目标。”
至于论文,他说:“论文固然很重要,但比论文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的学术能力有没有提高。我想同学们毕业时最重要的收获,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只要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即使这次没有成功,今后肯定会有成功的机会。归根到底,做出新的发现比发表论文更为重要。”
之后,大家又重新鼓起了勇气。这时候,李文辉的爱人、此前也在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病毒和抗体药物研发的隋建华加盟北生所。在她的帮助下,团队对“渔具”进行了改进:设计了一个单克隆抗体位点加在“鱼钩”上,便于定向追踪和捕捉。同时,严欢在原来的“鱼钩”上加一个“倒钩”,防止狡猾的“小金鱼”逃脱。经过改造后“渔具”不但有了强有力的“双保险”,而且也加了高灵敏的“跟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