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元稹,惭愧没能给出身高门的亡妻韦丛一份优裕的生活,叹爱妻生前,“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就在写这首悼亡诗《遣悲怀三首·其二》的同年,他就纳了妾。而且,他与当时才貌双全、久负盛名的名妓薛涛更燃烧起了一段浪漫诗意的旖旎情事。
再看那负有“中国千古第一文人”之盛誉的苏东坡,无论才学、政绩、思想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都可谓读书人中的完美楷模。他在妻子王弗去世十年后还依依提笔、梦回少年夫妻的轩窗,感人至深。但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到晚年,他又与爱妾王朝云琴瑟相谐,一段老少恋在文坛上留名千古。当他在梦中与亡妻“无语泪千行”的时候,早已在现实中与佳人“连朝语不息”了。
至于那个多愁善感的“满清第一词人”纳兰性德,能与他诗书应对的亡妻卢氏令他下笔缱绻、怀恋至深,连友人读后也称“容若词有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顾梁汾语)。然而就在旁人读诗也凄楚的时候,这些悼亡诗的作者纳兰性德,已经娶了一等公图赖的孙女官氏,恩爱甜蜜,夫妻和美。他在悼亡词里感慨失去了的、与亡妻曾经“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幸福片段,如今,又在新生活里把这些欢乐都一一地寻回了。
面对悼亡诗,从诗词漫想回归到实际生活,那些字句间引人入胜的凄美与现实中令人失望的平凡形成了残酷而真实的反差。向往完美的读者们在失落之余,不禁要质疑起悼亡诗的情感真实性与写作必要性:那些诗人们,既然感情已分散给新人,又何必念念不忘于旧人、惺惺作态呢?既然真心已转移至现今,又何必细细描摹着往昔、多此一举呢?
但是,请对诗人怀有失望的读者不必怀疑: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他们的写作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真情过,所以有资格祭奠这份真情。当他们拥有着的时候,用心投入过;当他们失去了的时候,伤心追忆过。对爱人,曾经,他们不辜负;后来,他们不冷漠。
这就够了。感情的尊严在于双方的真诚与平等;感情的价值绝不该用绑架某中一方心灵的自由和一生的意志来偏激地印证;感情的高贵在于奉献自我,而不是陪葬对方。
当诗人悼亡过去的爱人,他们既是在怀念也是在送别、既是在写实也是在升华生命里爱的箴言——即使已成为过去时。可是人虽往、情不灭,那一份情就此永恒于纸上、永远于心间,并不随亡人永别于人间。悼亡诗是在以血泪告诉世间:他们爱过,不负相遇、不负缘分、不负彼此、不负此生。
一生只接纳一个人、失去就为之守节终身,这样的愿望或许如童话般纯美,但这样的要求也可能如咒符般恶毒。连与丈夫志同道合、恩爱有加的宋代才女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离世后,也因种种现实问题而改嫁了他人。可见在实际生活中,要为亡者空白一生何等艰难,何况是那些比女性选择余地更广的男性。
感情对象的改变不是罪过,多情也不是罪过。滥情人肯定不会专情,而多情人往往懂得痴情,情能痴时,忆故与求新,都是情感的珍贵。
所以,即使后来诗人又有了新的情缘,那又与他悼亡的曾经,有何矛盾呢!前情与后情不是彼此重叠的混沌不清,而是各自专注的各负其责。悼亡过去,面向未来,不辜负把握幸福的能力,这本来就该是爱的愿望。
我们再看《绿衣》中的那位未亡人,他抱着一件旧衣凄凄以对,何等悲苦,何等哀凉!如果他怀念的妻子与他真的如此相爱过,无论那位妻子是逝世还是离开,都一定会祝祷这凄绝的男子可以重获幸福,不忍他的孤苦与悲凉。就像卓文君在写给司马相如的分手信中还要不免嘱托“努力加餐勿念妾”:勿念妾,我们从此分离;但是努力餐饭,请为你自己珍重。而苏轼的妻子王弗在病逝前,也愿将堂妹王闰之许给丈夫,她要让一个值得信任的女子来接替自己,照顾她将永别的爱人。
爱就是这样,爱一个人虽然不免会自私,但是更舍不得残忍。真爱,即使面对死亡,也是正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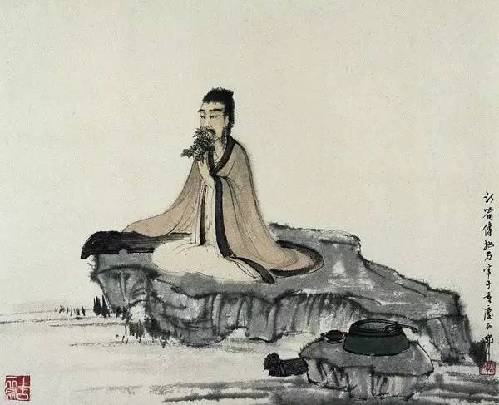
(四)旧物情深
《绿衣》这首诗共四段,每段都是从一件平凡普通的旧衣开始叹咏。这一件妻子留下的衣衫,成了诗人抱在怀中、撂不开手的至宝。《绿衣》由此奠定了一种怀念过去的方式,就是:寄今情于旧物。物是人非,便睹物思人。













